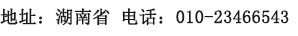中国文坛精英盘点之80后作家专辑
点击作家姓名,可直接阅读
周李立
甫跃辉
宋小词
陈崇正
宋小词
马金莲
刘汀
杜若
吕魁
于一爽
孙频
陈再见
朝颜
小昌
草白
侯磊
董夏青青
寒郁
曹永
西楠
李黎
杨莎妮
焦冲
钱佳楠
曹潇
毕亮
杨碧薇
周荣池
吴永熹
李德南
郭爽
赵目珍
徐艺嘉
蒋志武
张敦
栏目主编
郑润良
导读
一、名家点评
二、创作谈:我喜欢这份每天遣词造句的工作
三、作品:恐高
作者简介王玉珏,年生。先后在《江南》《芙蓉》《长江文艺》《解放军文艺》《芳草》《福建文学》《雨花》等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80余万字。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选载,曾获第四届泉城文艺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并入选多种年度选本。现供职于济南市文联。
一、
王玉珏的小说具有一种超出题材界限的包含和广阔。他的思考重在表现人性世界里的幽深和曲折,因为人物的立体,不但故事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品的深意也获得了切实可信的依托。总之,王玉珏对创作保持了自己足够的警醒,他要成为一个把人放在关乎题材、主题之前的小说家。他的创作前景大可令人期待。
——王方晨
王玉珏的军旅小说,辨识度明显。他擅于在螺狮壳里做道场,从一个个执拗的个体起笔,掌控叙事节奏、塑造人物形象的层次感及流动性。行文看似无事,却暗流涌动,在不经意间巧妙地编织了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诱得你不觉间就走进了他设置的迷宫。
——文清丽
王玉珏的小说是细嚼慢咽型的入胃,读者之所以愿意耐下心来品咂、琢磨,不仅仅在于情节的巧妙设置和精彩构思,更多的是在故事的壳表之下,他对社会现实的独特思考,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这种独特和深刻,并不显得声势浩大,也不显得咄咄逼人,而是渐进式的,螺旋式的,潜藏式的,也是王玉珏式的。
——林东涵
王玉珏的小说大都将人物置于某种境地而非故事里,这样的方式有难度且不易讨巧。相较于好看的故事,人物在某种境地中的际遇更加平面、琐碎和日常,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物的人性世界才获得更加精微和多侧面的呈现,从而实现“对内心真实最大限度的抵达”。
——颜慧
二、
我喜欢这份每天遣词造句的工作
王玉珏
我想,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种职业能够像写作一样与生活如此亲密无间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努力让它们井水不犯河水,并以此作为自身生存景况的一种标榜。但是对于作家而言,就要另当别论了,作家的生活和写作是互相高度介入的,它们之间界限模糊不分彼此,亲密到如此程度也许只有一种关系可以形容,那就是夫妻。
所以当你问一个作家他的生活和写作哪一样比较重要、谁更高于谁时,无疑就是等于问他,在家里他和他老婆(老公)谁说了算。这个问题显然不太高级。
大到生老、聚散、情仇、爱恨、小到风吹草动、柴米油盐、打针买菜逛商场,这些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是生活本身,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他的工作其实已经开始了,他一边生活一边在根据它们各自的规模来分配自己的关照和情感,他其实是在以双重身份经历他的日常生活,他在经历也在使用,他在忍受消耗也在接受馈赠,这是无比奇异的感受,就像冬天你用自己的手去焐自己的耳朵,你既感受到了你自己的温暖,也感受到了你自己的冰冷。
当然反过来也同样,当一个作家坐下来开始遣词造句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更多地不像是在工作,更像是在生活。哪里有这样的工作呢?写作作为一种职业而言它完全不符合我们常规意义上对其的定义和要求。首先它足不出户,纯属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其次,它可以被随时打搅和侵犯。
唯其强大,强大到不能被生活轻易打搅和侵犯,才能称之为工作,这是我的理解。我有一篇小说《跷跷板》,里面主人公有一句话就很能代表我的理解:“工作上的事才是大事,工作上的一个小拇指抵得上家里的一根大腿粗。”用在写作身上正好可以反过来,“生活中的事才是大事,生活中一根小拇指抵得上写作的一根大腿粗。”事实就是如此,当你阅读、构思、敲键盘的时候,生活中屁大点事都能叫你挪挪地方。比如,家里水电费煤气费该交了,比如老婆接送孩子打针幼儿园家长会,你不能以我正在写作为由推诿,那是最拿不出手的理由。拿不出手更多的时候恰恰不是在别人看来,而是你自己觉得,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在心虚气短。并且,这个跟作家的大小无关,即便是鲁迅和巴尔扎克,也免不了会被一声儿子的啼哭中断手里的巨著,即便这巨著将烛照人类百年。事实就是这样,写作就是这样和善、窝囊、理不直气不壮。
怎么能不窝囊呢?比起出差开会接待客户送外卖,比起其它一切正经而又理直气壮的职业,这个遣词造句的工作它一点都不省劲,更不省心,一样地需要你殚精竭虑,一样地也在挣钱养家糊口,久之难免时常会一赌气冒出冲动:换个工作!
这样的念头我就不止一次地经历过,尤其在更早以前。比如,当你无法确定是否可以有条件除了写小说什么也不干的时候,比如当你发现了文学的无力、世道的凶顽之后,但每每都是如此,在一次次经历了冲动和气馁之后,还是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原地,并且,正是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反而愈加发现了写作的不可替代。当写作真正成了一种日常和需要的时候,你才发现,它原来已经那么不可一世地统辖了我们生活中的全部。没错,就是如此,对于作家的生活而言,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前提,是背景和底色,是辐射和照耀,它让日常中的一切鸡毛蒜皮都变得熠熠生辉,让生活中的一切悲欢和福难都长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影子。
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恰恰相反,写作并不窝囊,它其实无比雄壮、必要和孔武有力。当你不再写作或者刚刚决定了不再写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好好的生活突然一下子变得不对劲了,变得索然无味,六亲不认。其实,不仅仅是作家,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是如此,我们都该为自己的生活找来一位相濡以沫的伴侣,有了他,我们在大地之上的一切言行才有机会获得别样的关照和意义。
三、
恐高
王玉珏
星期六陈娜是夜班,下午就出门了,到图书馆去占位子。上个月刚报了司法考试,复习正抓得紧。王耀汉在阳台上已经抽了午觉后的第三支烟。陈娜在门口一边换鞋一边嘴巴对着墙声音很高地提醒他,别忘了晚上提前半个小时去接果果。王耀汉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脑子里想这会儿钟良是不是也该起来了。
一中午都没怎么睡好。听到陈娜关门下楼的声音,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在等,等陈娜出门,也等几百里以外的钟良睡醒他的午觉。在决定给钟良打这个电话之前,王耀汉自己折腾了自己好几天。知道是非打不可的,还是免不了折腾。毕业已经快十年了。他多少有些后悔不该一时嘴快让陈娜知道钟良这个人。
大学里他跟钟良一个系,俩人都是霍山的。霍山县那年一同考进省师大的除了他和钟良,还有三个人,报到第二天就聚了头,自号“霍山五虎”。五虎结义抱团,表面上喧嚣,其实全部内容也就止于饭馆里的几顿酒肉,王耀汉跟钟良之间谈不上多少私交,五人里面,王耀汉只同一个宿舍的刘兴元相投。毕业离校前五虎的最后一顿散伙饭之后,钟良又另外请了王耀汉一顿,就他们俩,钟良单请他一个人。请吃是因为答谢,钟良的毕业论文是王耀汉过继给自己的,论文质量堪称上乘,本已是发表在即,为救钟良的急,王耀汉忍痛临时给编辑打了电话。请一顿饭本来倒也没什么,问题是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而且一顿饭花费不菲,比之前五个人加起来还多。稿费你不要就算了,人情我总是要还的吧。钟良恳切、坚决,目光里干干净净,实在是叫人无法推辞。
虽说有点小题大做,不过,王耀汉倒还是从中觉出了钟良身上的某种细致,这个人其实很多时候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粗枝大叶,不然也坐不稳厅长秘书这个职位。
按说霍山离省城也不远,一百公里多一点,汽车火车都方便,可是十年当中,他跟老同学加同乡钟良却只见过一次面,还是六七年前的事情了。那回是“霍山五虎”中的老四结婚,在霍山摆请。去的只有他和钟良,刘兴元跟另外一个临时有事没赶回来。没有了“霍山五虎”这面旗子,王耀汉和钟良都有些找不着感觉,寥寥的几句话都落在了客套的酒杯里。省城王耀汉倒是常去的,出差开会,有时一待就是个把星期,每次去都没想着拜访一下钟良。没这个心,电话也就不想打了。王耀汉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确实有点那个,早年不主动是因为钟良每次回霍山都不打电话给自己,这几年陈娜接她老子的班进了交通系统,成了钟良基层的基层,心里的曲折就又多了几分。
手机里存的钟良的电话有两个,一个是手机,一个是家里的座机。手机肯定是通的,每年中秋春节两个人都会照例转发个祝福,但王耀汉还是愿意打家里的座机,不然也不用专门等到星期六。
接电话的是时雅菲。一听就是她的声音,多少年了,还是当年校园喇叭里朗诵《赠朱丽叶》时的那般袅娜雅致,王耀汉自报家门,那头一张嘴竟失口叫了他一声“约翰”——这个洋名是“耀汉”的谐音,当年只有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时雅菲才这么叫他。王耀汉喉咙里就有点发紧。多少年了,没想到自己在听到时雅菲声音的时候喉咙还是会不自主地收一收。
有七八年了吧?
八年多了。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王耀汉笑着纠正道,不是见到,是听到。
一样的。对方很认真坚持,压低了声音问他,你找钟良还是找我?
他在吗?
在。
那,太好了。
不管怎么样,王耀汉还是觉得很庆幸,万事开头难,真地很难得,第一个电话就找到了钟良。
王耀汉没想到钟良答应得那么痛快,反而心里不踏实了。等了半个多月,果然一点动静没有。想再一个打电话问问,觉得不妥,不打又不甘心。陈娜在这件事情上从一开始就是急功近利的,这时还是她的主意,还是干脆去一趟,既然早晚都得花,不如花在前面。她现在也不每天往图书馆跑了,有了新的指望,吃苦的劲头一落千丈。王耀汉没有表态。不表态,其实就是默认的意思了。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两个人的分歧在于到底是买东西还是直接拿真金白银。陈娜一眼就看穿了王耀汉肚子里的那点绕绕,懒得陪他兜圈子,张口一句便捅到了底。
反正都是送——咱脱都脱了,还差最后那一件?
王耀汉的耳根一热,下意识地伸出两根指头捻了捻右边的耳垂。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一被人揭穿什么就会伸手去捻耳垂。他忽然想起来早几年有一次进洗头房的经历。几个老同学一起喝多了酒,非拉着他进去。女孩年纪不大,人倒很大方,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偏遇到了王耀汉这么一个华而不实的人,非要亲亲人家。女孩死活不肯,拳挡手推地,差点闹翻了脸。他当时心里想,摸都摸了,怎么还就亲不得?王耀汉脑子里现在跳出来的就是这句话。
陈娜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中午一下班就去了银行,回来交到王耀汉手里一张卡。她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两根指头叉得开开的,很悲壮地在王耀汉眼珠子前面摇了摇。这个数字是她所能接受的极限。
又等到一个星期天。他先发了一条短信给钟良,问他在不在省里。对方很快就回复了,说在,问他什么事。他心一横,手机往口袋里一塞就动身出了门,直奔车站。汽车驶离市区的时候,第二条短信才发过去:我来参加一个培训班。方便的话,晚上过去看看你。正准备摁下发送键,犹豫了一下,把最后的“你”删去了,换作了“老同学”三个字。
没想到钟良那头却没了动静。王耀汉坐在风驰电掣的公共汽车上,每隔两分钟就把手机掏出来看一看。他尽量朝好的方面想,也许是钟良突然临时有事没看到短信,或者看到了还没顾得上给他回。他本来打算再发一条,想想还是忍住了,反正人已经在车上。下车时才两点多,太阳还很高。午饭没吃,现在却一点饿意也没有。他记得车站停车场对面好像有一家肯德基,不吃不喝也坐得住,绕了一圈却没找到。不知是自己记错了,还是挪了地方。
王耀汉掏出手机来,决定先给姑妈打个电话。不管晚饭过不过去吃,觉总是要去睡的。姑父人礼数多,自己三五年难得到家里去一趟,隆重点好。指头刚触到键盘,它自己却响了。是钟良。钟良解释说,刚陪领导从工地上回来,短信没看到。又问,报到了没有?王耀汉忙说报到了报到了。钟良问,培训几天?王耀汉突然有了一个直觉,今天晚上够呛能见到钟良了,回答的时候就给自己留了些余地,说,还得看情况,培训就两天,后面安排了几个活动,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要参加。果然钟良的口气就舒展了些,说,那这样最好,晚上就不给你接风了,一会厅里还有个活动,脱不了身,过个一两天我再打电话给你,我和时雅菲一起请你吃饭。王耀汉心里又凉下去一截,嘴上却只能客气再客气。挂了电话,再接着打姑妈家的电话。没人接。过了五分钟再打,还是没人接。又打手机,姑妈的声音在电话那头高亢而遥远。人正在南京,夫子庙,吃油炸臭豆腐呢。昨天的火车,姑父单位组织了百年不遇的一次老年游叫他赶上了。
同学熟人倒是还有几个,王耀汉也不想联系了,自己这趟来名不正言不顺,又不好跟人透底,谎话套谎话自己也嫌累。反正也就一顿饭,在哪吃不是吃。住也简单,从车站往东步行几十米,一条街上的宾馆比水果摊还多。
第二天醒来,已经九点多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好觉。王耀汉有个习惯,一住宾馆就很依赖电视,平素里只觉得粗鄙乏味的电视剧在异乡的深夜里一个人倒能看出不少暖意来。昨天一直撑到一点多,眼皮抬不起来了才关掉遥控器,倒头就睡,睡眠质量比在家里那张床上高了不少。快到中午时陈娜打来了电话,劈头就问,接上头没有?王耀汉煞有介事地打了一个哈欠,说,昨天省里给培训班接风,一下车就被拉到酒店去了,快十点了才散——他提前三四天就跟陈娜打过招呼,说周末要到省里参加培训班,怕的就是这种局面。陈娜打断他,口气有些不耐烦,最好是到家里去,办公室也行。别在饭桌上,饭桌上都是乱七八糟的人,又喝酒。王耀汉心里嘲笑着陈娜的自以为是,含糊了一句,我心里有数。本来还想问一句果果,周一下午幼儿园组织打疫苗,感觉到陈娜不想同他多说话,估计是心疼漫游的电话费,也就算了。
在宾馆门口的快餐店里要了半斤水饺打发了午饭,回来接着看电视。一直等到快五点,钟良也没打电话来。王耀汉这才意识到昨天钟良在电话里说的那个“过个一两天”估计是不包括今天的,不然他怎么不直接说明天呢。空调一整天都响着,开着的时候不觉得凉快,关了又觉得热。身上粘津津地,脚丫子却冰凉。窗帘拉着,但还是能感觉到外面的天在一点一点黑下来。
天完全黑透了之后,王耀汉出了门,来到马路旁招手打车。他告诉司机去凤凰小区。凤凰小区其实就是交通厅的家属院。电话里钟良顺口提了一句,王耀汉当时就记在了心里。
从没来过,第一次。司机说是就是了。下了车王耀汉隔着马路朝对面打量,半天也没找到“凤凰”两个字,或许有,晚上看不见。他掏出手机来给钟良打电话。钟良说自己正在外面吃饭。这倒是实话,电话里有股酒气。王耀汉哦了一声,表示失望,也是真地失望,嘴上还得坚持下去,本来想上去坐坐的,刚吃完饭,他们送我回来,正好路过你们小区门口。钟良笑声朗朗,老同学你这就叫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没去看你,你倒来看我了。王耀汉愈发底气不足,马上说,这不赶巧了么,正好顺路——要不,我等等你?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这话已经很露骨了,尤其是又多了后面的那句画蛇添足。到底还是不甘心。钟良那头却还是油盐不进,一连声地说,别等别等,千万别等——话筒里有椅子拖地的声音,估计在起身,果然再开口时里面的嘈杂减去了不少。今天晚上还不晓得拖到什么时候,一会结束了老板说要打几圈牌,我还得陪。要不,这么的,明天。明天我来安排,你等我电话。今天算是预约,你有活动就往后推一推,把明天晚上留给我。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他王耀汉还能再说什么?一天一夜就这么白白扔在宾馆里了,还有明天一整个白天。王耀汉倒并非心疼时间和房费,只是觉得有点窝囊,心口里有股多余的东西无处遣送。已经九点多了,街上车还是很多,一辆接着一辆,鱼贯来去,车灯晃人的眼。其实,本来也可以把电话直接打到家里去的,如果时雅菲在,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上去坐一坐。当然也就只是坐一坐,喝喝茶,说说话,他是不可能通过时雅菲把那张卡送出去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可能把卡交到时雅菲的手上,哪怕陈娜的事情不办。这条底线,他还是要给自己留的。
第三天碰上了“五虎”之二刘兴元,在网上。这倒是意外收获。起床之后,他去服务台预交房费,回来时看见服务员正在房间里打扫卫生。他在门口站了一站,看一时半会结束不了,突然心血来潮,决定出门找一家网吧打打牌消磨时间。反正也没事做。
刘兴元正好在他的QQ里,刚改了签名:“成功是99%的天才加上1%的努力”,就顺手敲了一句过去,我现在就剩那1%了。对方发回来粗粗大大的两个问号,并不知他所云。刘兴元没事就换签名,换得多了有时候自己都忘了。王耀汉便懒得与他再多话,刚想隐身起来斗几把地主,对方忽然问,公干还是私事?
王耀汉正莫名其妙,对方接着又是一句:
我也在省里,快一个星期了。
王耀汉这才想起自己的IP地址显示是当地的,难怪刘兴元那么问。他没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里,先问了一句刘兴元,你怎么跑来了?
对方回了两个字:截访。
刘兴元毕业后第四年考上了公务员,异地任职,进了霍山邻边的左源县交警支队。左源这两年大兴土木,像堆积木一样到处盖房子,有本事拉却没本事擦自己的屁股,弄得几个村的小老百姓要么上吊要么上访,县里的公安也跟着受累,省里北京到处撒人,有时在火车站一蹲就是半个月。人手不够,连交警都派上了。
刘兴元不了不休:到省里来高就了?也不说一声。
跟刘兴元没必要藏着掖着。屁,私事。到两天了。知道对方还会往下追问,干脆主动交代了:我老婆的事,来找钟良。刘兴元知道陈娜现在跟钟良在一个系统,估计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其它的便不多说。也不想说。
刘兴元问:现在在哪?
网吧。
哪个网吧?
进来时还真没注意,这时王耀汉在座位上伸长了脖子找了一圈,吧台上“星世界”几个大字星光四射,应该就是网吧的名字。
刘兴元发来一个龇牙咧嘴的笑加一个酒瓶子:中午的饭着落了没?坐坐?
王耀汉想都没想就敲了赞成两个字过去。他乡遇故知,也算一喜。心情忽然振奋了不少,干脆掏出电话打过去。一问,离得原来不远,就隔了两条街。刘兴元让他回房间等,一个小时以后自己开车过来。
卫生早收拾完了,房间里焕然一新,跟住进来之前一样。本来想就势往床上一躺的,临了屁股还是坐在了沙发上。房间越干净倒是越叫人放不开手脚。遥控器刚拿在手里,短信来了。是陈娜。
陈娜问他到底是不是来参加培训班的,怎么跑到网吧去上网了?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接着又是一条,果然说,我往你们值班室打电话了,小袁接的,没听说什么培训班。不知道是哪里露了馅。王耀汉拇指搁在键盘上,正犹豫着该不该说实话,有人敲门,急吼吼地。必是刘兴元无疑。
刘兴元是带着一泡尿赶来的,门一开就一头钻进来,胳膊里夹着茶杯,径直进了卫生间。门也不关,站在那里五大三粗地边放边说:
饭吃不成了。刚接到情况,一点半就得上国道。我过来找你聊两句。
到了饭点还不卸套,属驴的你们是。
刘兴元抖擞完毕,洗了手出来,驴忙。还没见着钟良?
王耀汉笑笑,给自己圆场说,刚当上秘书,也忙。
嗯忙,人家是忙。他现在比谁都忙。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脸的别有意味。
你也要找他?
找过。
谁的事?
也没谁的事。
刘兴元不想多说,他也就不好再问。刘兴元从来没跟他提过他跟钟良之间的来往,今天如果自己不问,估计他也不会提。论旧交,过去他们两个跟钟良也都是半斤八两,三个人里头,当然也是他和刘兴元近,但现在社会上都在流行抱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么,刘兴元再不济也是穿制服的公务员,而且交通和交警本也是近亲。王耀汉知道自己一向敏感,怕联想得多了,平添烦恼,把话就岔开了,说起这两年交警待遇的问题。前一阵新闻上报道了省城一个区里的车管所副所长被抓的事。王耀汉窥斑见豹,一个区里的车管所,论级别能不能够得上股级?还是个副所长,两年就搞了七八十万。刘兴元倒也性情,当着外人并不向着自家,抱怨说如今世风日下,大不如以前了,马路上车越来越多,油水却是越来越少,工资卡里的钱不动是不可能了。好一个世风日下,王耀汉忍不住笑出声来。
王耀汉看刘兴元不停地掏手机,也不知道他是等电话还是看时间,就说,你有事就先去忙,中午不行,我们再找个时间。
刘兴元说,那晚上?
晚上怕不行,王耀汉照实说,晚上约了钟良,难得人家抽出空来。要不,咱们一起?
你找他办事,我去掺和做甚。
这方面刘兴元向来是聪明人,王耀汉心里有数,嘴上还是又坚持了一句,那有什么的,又不是外人。自己都觉得自己虚伪。
刘兴元暧昧地笑笑,去了就成了外人了,人家现在对我是敬而远之。
这话怎么说?
刘兴元把目光避开了,低下去帮着嘴巴到茶几上去找茶杯。并不解释。也许不太好解释,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王耀汉越来越有个感觉,这个刘兴元跟钟良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些什么,或者有过什么。不一定跟自己有关系,但肯定有。他也不想让自己对此表露出太大的兴趣,起码看上去是这样。如果愿意说,不用问刘兴元自己也会说,如果不愿意,逼得再紧也没意义。
刘兴元抿一口茶,目光从杯沿上面抬起来,你这趟是专门跑来的吧,有没有把握?
王耀汉摇了摇头,说实话,这趟来,我也是有枣没枣打一竿。毕业这么多年我一次电话也没主动给他打过。平时不烧香,就凭同学关系这点老底子,关键时刻人家佛脚未必肯给你抱的。
烧了香又怎么样,也未必就让你抱。
那总归还是不一样。佛心它也是肉长的吧?
我也说句实话耀汉,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你我,还是在人家。你懂吧?刘兴元把脸板起来,撵走了上面所有多余的表情,难得的庄重,这人位置不一样了,想法也跟着变。有些时候,在我看来,有这层关系倒还不如没这层关系的好。这是我的体会,你参考。正因为不是外人,知根知底,人家反而不愿意往身上惹。跟你说件事。钟良毕业之前曾经让派出所抓过,因为嫖娼。不知道吧?
嫖娼?
这事只有我知道。临毕业的那年。刚放寒假,你们都回家了,我还没走,刚跟孟洁好上,舍不得晚走了几天。有一天半夜,十二点多了,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叫我带五千块钱去派出所领人。就是文化路那家派出所,所长姓欧阳,复姓。我估计派出所其实就是要钱,拿钱就放人。不拿钱第二天通知学校来领,反正学生证扣着呢。他知道我当时卡里有钱,准备买电脑的。回来他死活不叫我把这事往外说,差点下了跪。谁都不叫说,说马上快毕业了,弄不好毕业证都拿不到。
王耀汉很吃惊,说震惊也不为过。主要还是觉得意外,这事居然发生在钟良身上,而且还是十年之前的那个钟良。刘兴元光天化日之下冷不丁地从嘴里吐出这么一个钟良,确实很难对上号。
刘兴元从口袋里摸出烟,知道王耀汉不抽,也不客套,自己掏出来一根点上。这事算我帮了他一个忙,本来是他欠我的一个人情,没想到,适得其反了。去年我老丈人家拆迁,想在镇上盘一个门头房,差七八万块钱。当时没跟你开口,知道你的情况。这事我找到他了,借五万。这事找他最有把握,已经当上秘书了,而且时雅菲的家境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他当时倒没一口回绝,说这事回头跟时雅菲商量。我当时一听有戏,心里一高兴就多了句嘴,说我当年宁可电脑不买都把钱借给你了,现在兄弟有难你也得帮一把。这就是一句玩笑,凭良心说,我是压根一点那方面的意思都没有,是他自己想多了。我是后来才慢慢琢磨过来的,过了两天,打他的手机,打不通。关机。隔两三天打一次都是关机。后来有一次我用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一打就通了,他没料着是我。我提借钱的事,态度像换了个人,名字也不叫了,一口一个老同学,说现在正在装修房子,五万块钱暂时拿不出来,自己手里倒是有现成的两千,让我先拿去用。我挂了电话再用手机打,又是关机。我这才明白过来,他把我的手机号拉到黑名单里了。这是防着我了。
不至于吧,都过去十年了。
可能有案底的。
那也不至于。
究竟至不至于,王耀汉自己其实也拿不准,单是十年之前的那个钟良,自己所了解的和真实的之间出入就如此之巨,更况乎十年之后。有一种人就是这样,他永远都会叫你拿不准。十年的时间不算短,更何况还是钟良的十年,今天的钟良不管成为什么样子,自己都不会感到意外,也不应该感到意外。
你也不用觉得太意外,这人到了高处,就是小心。
什么小心,是小人之心。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咱话说回来,也可以理解,这人太顺了,上位太快,就怕被盯上,也容易被人盯上。前一阵子网上不是挺热闹,说有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市团委书记被人举报毕业论文造假么?平头老百姓谁闲着没事捣鼓你?像他们这种人,但凡有点不光彩的历史,都恨不能一笔抹掉。
提到论文这两个字,王耀汉脑子里突然就跳出来自己当年割爱把论文过继给钟良的那件事,再琢磨刘兴元前前后后那些话,心里就有点发沉,像有只突然横过去的手搁在了那儿。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刘兴元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忽然又转过身来,对了,忘告诉你了,刚才在网上碰见你老婆。她是不是不知道你来?
王耀汉这才想起刚才陈娜发来的短信,明白原来问题出在这里。送走刘兴元回来,没再犹豫,很快把短信回了过去:
我最迟明天回去。最好有个思想准备,情况不太乐观。
那种不好的感觉果然应验了。午觉刚醒,三点多一点,钟良打电话来了,满口隆重的歉意。刚接到通知,厅长要去白马市出席一个开工仪式,今天去明天下午回来。马上就出发。
你培训班什么时候结束?
因为有思想准备,王耀汉此时并不觉得多么意外,口气也是淡淡地,我们明天。没事,你去忙你的,等下次吧。
等下次吧。这趟真是不巧,连顿饭都没请你吃。
王耀汉等钟良主动提上次自己跟他说起的陈娜的事,于情于理都应该提一下,可是钟良真地就只字不提。他不可能不清楚自己这前前后后的心思,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了。王耀汉心中仅存的那点侥幸也荡然无存。
挂了电话,王耀汉心里突然就冒出来一个猜测,钟良之所以也对他“敬而远之”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都知道,当年的“霍山五虎”中自己跟刘兴元关系是最近的,俩人又同住一间宿舍,他会不会以为当年刘兴元一定把那件事告诉自己了。并且,还有,当时他不惜跪求刘兴元让他为自己守密,担心的也许并非仅仅是一个毕业证——花钱消灾,人反正已经出来了,学校和派出所也没必要对他不依不饶——他真正的顾忌可能还是时雅菲。从时间上推算,那时应该正是他和对方的关键时期。
事情至此王耀汉反倒轻松了,该尽的力都尽了。除了一趟奔波之苦和车旅费,也没什么损失。也算不上什么损失。至于陈娜那里,编个像样些的借口搪塞过去就是了,陈娜这个人他了解,热起来快,凉下来也快。看看时间,还不到四点,现在去车站还能赶上回霍山的车。立刻收拾东西。临出门时忽然想起来,应该跟刘兴元打个招呼,道一下别。他打了对方的手机,谎称下午已经见到了人,在交通厅门口的餐厅里喝了茶。电话里车水马龙的,刘兴元正忙,别的也没多说,就问房退了没有?王耀汉说,正准备退。刘兴元马上说,那就别退了,再住一天,晚上我没事,一起吃个饭,正好手里有两张华威达的五折券,不去可惜了。王耀汉本意是想推掉的,只是一时没找到很过硬的理由,嘴上耽延了一下,也就只好答应下来了。
去之前王耀汉并不知道刘兴元的五折券是在华威达的顶楼旋转餐厅用的,不然就另选地方了。华威达他倒是知道,来时的高速路两旁就有它的广告牌,三个金色大字,高高地立在那儿,一副飞扬跋扈的样子。省标建筑,五十七层,全市最高的酒店,档次也高,一般的老百姓不会自己花钱到那里去请客,自己花钱的,也不会是普通老百姓。从没听说过顶楼还有一个旋转餐厅。
倒不是嫌它贵,再贵也不是自己花钱,更何况还有五折券。主要是高。王耀汉有一点恐高症,从小就有,人一凌空腰就直不起来。也算不上多么严重,日常生活中也没那么多的登高爬上,平常家里擦个玻璃、换个灯泡,都是陈娜。除了父母和陈娜,谁也不知道,也没必要让人家知道,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一个男人。
其它事情上也就罢了,仅仅是为吃顿饭,受这个折磨似乎有点不划算。确实是高,光电梯就坐了五六分钟。每隔两三层就停一下,放几个人出去,再放几个人进来。显示楼层的指示屏,就像量血压的血压计,王耀汉看着它上面不断攀高的数字,心脏像被一根绳提着向上拎。干脆把眼睛闭起来。
落座的时候王耀汉坚持挑了靠过道的一张桌子。来得尚早,一半的位子都还空着,刘兴元似有不甘。一般人来这里大都喜欢靠窗,边吃饭边一览众山小,是一种享受。圆形的餐厅是旋转的,每五十九分钟一圈,坐地不动便走在分针前头。设计者慧心绝伦,王耀汉辜负了。翻着菜单,王耀汉既是解释,也是解嘲,对刘兴元说,我这人胆子小,一到高的地方就怕,没出息。打小就这样。你将就将就我。这么贵!不就是炸茄盒么。
一道肉蓉金茄标价六十八,确实不菲。
放心,剩下的那五折也不用你掏。你身上的一分也不动你的。
这里刘兴元是接着之前的话题。来的路上在车里刘兴元已经问了他下午喝茶时钟良的态度,王耀汉怕露了马脚,不敢说多了,只含糊地告诉他钟良说答应试试看。刘兴元当着司机一点也不避讳,问他收了没有?听说没收,鼻子一哼,嘴里当即就很响亮地甩出来一句粗话。
刘兴元从对方手里拿过菜单,一气呵成,很快把菜点齐,等服务生转身走开,脸上马上又堆起一把不屑,你说你胆子小,我看,钟良胆子比你还小。
王耀汉想着在刘兴元这里为自己的面子留些后路,这时还是那句话,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人小心。
这次刘兴元没再接着说什么“小人之心”之类的话,目光漫不经心地在王耀汉脸上兜了一圈,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跟他提了我在这里没有?
谁?
钟良啊。
哦。没提,怎么了?
没提最好,别跟他说我也在。
王耀汉打趣道,现在到底是他躲着你还是你躲着他?
刘兴元倒严肃起来,以前每次来省里,我都给他打电话,自从上次那事出了之后,我一个电话也没给他打过。太明显了也不好。不管在不在人家的黑名单里,咱自己不能授人以柄。世界就这么丁点大,说不定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就狭路相逢了,你不一定能指望他作为,但说不定还有需要他不作为的时候。这个道理咱都懂吧?
王耀汉笑了笑,兴元你也是小心之人。
小心其实也没错,小心驶得万年船。第一道菜上来,刘兴元为之一振,马上抬臂把盏,把表情和口气都调整到了位,来来来,老同学,第一给你接风,第二为咱们老友重逢。两个意思绑一块。干了。
要的白酒。王耀汉平时酒量优柔骑墙,喝多喝少全仰对方,你敬我一尺,我就能回你一丈。转眼就是三四杯。身子开始渐渐发轻,重量都跑到了脑袋里。刘兴元连目光都轻了,服务员上菜,转身离开时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短裙包裹下的一团紧俏,很无耻的样子。王耀汉用筷子把他的目光勾回来,放在对方面前的菜碟上敲了敲,这才几杯,就乱了性?
刘兴元脸转过来,目光里的那几分下流依然未消。
这次来,没会会老情人?
王耀汉知道他说的是谁,故意装糊涂,会谁的老情人?
你少装糊涂。
王耀汉知道,这种事越是摆到了桌面上就越是严肃不得,一严肃味道就变了。他避重就轻,故意用了孟浪一些的口气说,那不得分个时候?这趟来人劳马顿的,暂时没那份心情。
你不是没心情,你是压根就没朝那方面想。我说的没错吧?刘兴元酒醉心不醉。
王耀汉不置可否地一笑,我来求人家办事,还想着去找人家老婆,这我成什么了?
这儿过不去?刘兴元用手里的筷子往自己心口那儿戳了戳。
是,不太地道。
那得分谁,老同学,你不要忘记,是人家对你先不地道的。当年论各方面,钟良他哪如你?
王耀汉干笑了两声,反客为主地端起酒杯来,举在自己和刘兴元视线之间。
刘兴元把头向一旁偏了偏,我说句实话,刘兴元每次推心置腹之前都要习惯性地用这句话开头,好像之前说的都不是实话一样,你就是太地道了,让钟良那小子钻了空子,不然弄不好,时雅菲现在就是你老婆,你就是现在的钟良。你说你当年也是,人家主动叫你到家里去,就你们俩,你去了就屁股坐在床上喝了杯咖啡。你这地道得也有点太那个了。
旁观者清。当年他跟时雅菲、钟良之间的前前后后,刘兴元一切看在眼里。见证人。也好在是刘兴元,若是换了别人当面对自己说这些,王耀汉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坐得住。当局者也不迷,似乎也并不能归咎于具体的哪个人,不能全怪钟良,凭良心说,当然更不能怪时雅菲。人和人的活法不一样,说到底爱情也是活法的一部分。又回到了那个自己一直在里面折腾了多少年的老问题。
我说了我这人没出息,眼里就那么一亩三分地。高处的东西不去想,也不敢想。
现在想也不晚。现在机会不是来了?
什么机会?
钟良跟时雅菲现在有问题。大问题。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又装糊涂?
王耀汉抬起头来,什么问题?我真不知道。
好长时间了,现在正闹离婚呢。我听我们家老孟说的,去年她们历史系有个聚会,好几个人都听说了。听说两个人现在都不在一个床上睡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是,结婚七八年了,连个孩子也没有。
王耀汉很努力地嚼着嘴里剩下的半口菜,嚼得不知所云。胸口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撞,撞过来又撞过去,潮声四起的。脸上却还是一堆空荡。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说没关系就没关系,你说有关系它就有关系,刘兴元把脑袋探过来,那抹标志性的刘氏暧昧又爬上了嘴角,哎,你有时雅菲的手机号么?
没有。这句倒是实话,确实是真没有。
我有。你要是要,现在就可以给你。
王耀汉还没来得及说出那两个字,刘兴元已经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了,自顾自地埋头在上面翻找起来。王耀汉本能地想去阻拦,嘴张开了却什么也没说出来,舌头像被什么拽住了。很快,裤兜里的手机短信来了。嘀嗒,嘀嗒,两声清脆的廊檐滴水,惊心动魄。他把它拿出来,时雅菲,三个字,字如其人,一样的洋气和香艳,后面跟着一串长长的数字,它们形貌各异地比肩站在一起,像一群正摩拳擦掌准备为他效命的敢死队员。
钟良不是去白马了么?正好。干嘛白白跑一趟?当年他挖你的墙角,你今天也挖他一回。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正好十年。扯平了。
王耀汉的耳根立即就红了,幸好喝了酒。他伸出两根指头来开始捻自己右边的耳垂。捻了一遍又一遍,像是在跟什么较劲。目光渐渐抬起来,端了很久,最后还是掉下来,耷拉着,很沧桑也很安静,仿佛走了很远的路。
我是来给陈娜办事的,不是来挖人家墙角的。
刘兴元一口茶差点没抿住,茶硬咽下去,把笑放出来。这笑来得凶猛,由于惯性巨大半天才踉踉跄跄地停下。
老同学啊老同学!
一瓶五十二度的洋河蓝色经典已经见底,还有两瓶啤酒,一人一瓶,依次打开,各自倒满,酒沫溢出酒杯,酒精在血液中荡漾。应该说,酒确实是个好东西,不仅能乱性,还能壮胆,能让你言所欲言、掏心窝子。刘兴元朝王耀汉举起杯:
老同学,今天,有句话我还真得说。
什么?
你,行,是个爷们,刘兴元伸出自己的一根大拇指,很是郑重地在对方眼前亮了亮,说实话,挺佩服你,真的,我这么说没别的意思,很真诚。这事换了我肯定做不到,为了自己的老婆来求人,拿热脸贴人的冷屁股,还是自己过去女朋友的老公,那得算情敌吧。你是个爷们。比钟良爷们。
实话确实不好听,即便再真诚。尽管喝了酒,两个人都喝了,王耀汉还是感到被扎了一下。他不知道该不该为自己辩护,也不知道该怎样辩护,酝酿了许久,一张嘴竟也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声音和目光都落在自己面前的酒杯里,既是说给刘兴元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这人呢,高处有高处的活法,低处也有低处的活法。
从华威达出来,与刘兴元告别,王耀汉一个人打车回宾馆。还是回到平地上的感觉好,踏实,稳妥,靠得住。窗户摇开,夜风欢欣鼓舞地灌进来,一股通透的清冽。酒已经醒了大半。出租车穿街拐巷走了十来分钟,在一个路口停下等红灯时,王耀汉抬头看见右边街灯旁的一个广告牌,宏达家居,居字坏掉半边,下面的那个古字不亮了,成了宏达家尸。昨天就是这里,当时自己还在心里骂了一句。他问司机,这儿是不是离凤凰小区不远?司机说是,往左拐,一两百米,一脚油门就到。他的手就下意识地伸到裤兜里摸到了手机,心脏很猛烈地跳了一跳,耳朵都能听见。如果,钟良真地去了白马呢。
红灯闪烁,绿灯亮起,车子缓缓起步。司机侧过脸来问,去哪,直走还是拐弯去凤凰小区?
他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调整了一下坐姿,轻轻吐出一口酒气,对司机说:
——直走吧。
重庆当代作家研究中心
主管单位:长江师范学院
年第89期(总期)
文中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文学院院长:丁世忠教授
中心主任:周航教授(博士)
副主任:肖太云教授(博士)
研究人员:梁平教授、付清泉博士、张玫博士、杨红副教授(博士在读)、王士琼博士、张慧强博士、高明博士、龙吟娇博士
网络总编辑:徐镇
网络副总编辑:唐艺引
编辑:喻淼、林千汇、杨露、王艺、谢唱、何世杰
本中心立足重庆,辐射全国,推出当代研究和评论文章,以及当代作家作品。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