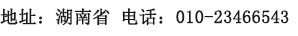点击“当代敦煌”蓝字 李云鹤到了莫高窟后,时任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对他说:“莫高窟刚好需要人,你就留到莫高窟工作吧。”李云鹤非常高兴接受了常所长的安排。常所长还希望李云鹤把他一同前往新疆的山东同学也叫过来两个,可是李云鹤叫谁,谁都不来。同学们都恋着大部队一起前往新疆,当然也嫌敦煌这里太荒凉。”
“在哪里都是工作。我便留在了莫高窟。当时,所里招了三个学徒工,包括我在内。新参加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所里三个月的实习考察。主要工作是烧开水、打上班的铃和打扫环境卫生(包括洞窟卫生)。那两个同志都说不敢进洞窟,那我进洞窟打扫卫生吧。说来也怪,我在家里胆子特别小,天一黑就不敢出门,但我被洞窟里上千年前古人巧夺天工的绘画和雕塑给惊呆了。于是,我干工作的热情更高。清扫沙尘,一层又一层,用牛车往外运沙子。就这么认认真真干了三个月。到了研究学徒转正的日子,研究所组织所里三十多名职工召开大会。大家一致表决同意我转为正式职工。三个学徒只有我一个通过。工资变了,工作也变了。转正后的当天,常所长对我讲:莫高窟就是壁画和彩塑,但是病害相当严重,小李你以后就做修复壁画和彩塑的工作,知道你还不会做这项工作,但只要你愿意去下工夫去学就行。听常所长这样说,我高兴的不得了,立刻表态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李云鹤先生在修复文物
由于历史原因,莫高窟曾经长期无人看管,过路的人,放羊的人随意到洞窟里面躲风沙,住宿,生火,乱刻乱画。最初的文物保护其实就是拆除窟前的乱搭乱盖和窟内搭建的土炕土灶,清除了几百年拥塞在洞窟内的大量积沙,同时还着手整治荒芜的环境,为重要的洞窟安装窟门,并在窟区修筑围墙,防止其再次遭到人为破坏。
“当时,研究所有三十多名工作人员,真正搞文物保护的人仅有三四个,他们都是美术艺术类科班毕业,其他的工作人员不长在莫高窟,都是跑日常业务的。”
李老山东口音很重,性格开朗。我们一见如故。说起往昔这段经历,他笑眯眯的样子很是亲切随和。看得出李云鹤老先生心情很好。
李云鹤刚到莫高窟,住的是原来饲养牲畜的马厩,房间内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制家具:睡的是土炕,用的是土坯做支架的桌子和书架和土坯砌成的沙发。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更没有卫生设备。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常书鸿先生同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生活,这就是榜样。不久,李云鹤生病发烧,同事刘宗文陪他一起骑着毛驴去县城看病,路上遭遇一只饥肠辘辘的野狼,他们和狼僵持了两个多小时,危情紧迫,他们险些被大狼吃掉。
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经过风化和氧化,形状和颜色都会变。莫高窟也一样。
莫高窟年代久远,材质是泥土的,十分脆弱,病害多。起甲、泡状起甲、颜料层脱落、粉化、疱疹、龟裂、裂隙、盐霜、酥碱、空鼓、地仗脱落、微生物损害,这些病灶都是莫高窟壁画的“病因”。特别是“起甲”,据统计莫高窟约有个洞窟、平方米的壁画有此病害。
“起甲”这种最严重的病害,如果不去尽快给它“治病”,它会一块一块脱落很厉害。
李云鹤最初的工作就是修复“起甲”的壁画。
李云鹤先生在加固维修雕塑
一个完全外行的高中生,对于壁画是怎么画上去的,雕塑是怎么做上去的这些工艺,他一无所知。更别说修复壁画这项工作。从零开始修文物,面对巨大的难题和困难可想而知。
好的修复,并非像人们所想的“清洁”和“黏合”这样简单就算完事。它首先需要对不同时代的壁画或雕塑的内容、表现形式和风格特征有真切的体会,还需要对原壁画绘制的过程或原雕塑塑造的程序分析了解,并对当时绘制壁画所惯用的工具、材料做深入的了解和运用,有了这些基本的掌握和熟悉后,通过实际的应用,才能把残缺的部分修复好,才能保持原作的历史风格,以达到真实传递敦煌历代壁画或雕塑艺术原貌和本质的目的。
当李云鹤认识到这些后,他大着胆子找常所长要求学画壁画,学做雕塑。常所长问他:你想当美术家?还是想当雕塑家?李云鹤坦陈直言:我既不想当美术家,也不想当雕塑家,我是要了解壁画是怎么绘制的,塑像是怎么做出来的,地仗是怎么做上去的?这样我才有信心和能力把“有病”的壁画和雕塑修复好。常所长说:你还有这个想法,好啊!
李云鹤先生与年轻工作者在修复壁画
于是,常所长安排李云鹤跟美术室的史苇湘先生去学习绘画。白天他们上洞子画画,晚上学习素描和练习毛笔字。除了吃饭,所有时间他都用来学习。一年后,他有了一定的绘画基本功。随后,常所长又安排李云鹤去学雕塑。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国家美术馆派了一个搞雕塑的工作人员临摹窟的塑像,李云鹤从打石膏,塑形,到上彩,整个过程都参与学习和制作。他,很快出“徒”了。
从此,李云鹤的使命才真正开始。
二、“摸着石头过河”,他发明了修复壁画的工具
世界上再很难找到两件一模一样的壁画和雕塑。敦煌莫高窟个洞窟中的40平方米壁画和0多身彩塑,每一幅(尊)都是穿越古老时光而来,不可复制。实际上,你看到的精美壁画,都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的修复。
最初莫高窟研究所的修复技能和条件仅限于对壁画脱落暴露的岩体进行抹泥处理或用十字铆把壁画固定回去。为了让修补的地方不太突兀,还在十字铆钉上进行了彩绘修饰。
不仅如此,给壁画打针用的粘结材料也不是一般的黏合剂,敦煌研究所时常要经过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才能筛选出与原用性能相近的胶结材料,这样才能保证粘得牢、不脱落。李云鹤他们当时用十多种材料在壁画上做实验,最后选了一种复合型材料,基本能够保证壁画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由于技术水平还不尽完善,如今,莫高窟的一些窟洞内仍有当年的十字铆钉存在,且还有发挥着固定壁画的作用。
工作环境
六十年代莫高窟研究所在全力进行石窟加固工程之外,对壁画和塑像的加固维修也同时大力进行。修复材料不过关也是当时工作中无法逾越的另一道“坎”。
年7月,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受文化部文物局委托,来到莫高窟进行壁画保护情况考察和壁画病害治理示范。这是莫高窟历史上迎来的首个“治疗”壁画病害的“外国医生”,对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美术组、保护组业务人员来讲无疑是雪中送炭,当即决定到第窟做试验,李云鹤被安排到现场观摩学习。
外国专家采用的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打针修复法”,能使起翘的壁画变得平整,非常适合莫高窟壁画病害修复。可专家对壁画修复材料及核心技术总是含糊其词。
李云鹤有心又聪明。他把外国专家所运用的材料仔仔细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重复专家的修复工序:把黏接剂用一支医用粗针管顺着起甲壁画边缘沿缝隙滴入、渗透至地仗里;待壁画表面水分稍干,再用纱布包着棉球,轻轻按压,使壁画表面保持平整、粘贴牢固。
李云鹤先生与年轻工作者在修复壁画
看起来简单的操作,实际上没有那么容易。
当时研究所还没有实验仪器,李云鹤便采取蒸、煮等高温方法观察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变化,还把材料放在室内室外、山上山下,分别在炎暑寒冬、白天黑夜进行对比观察,最终获得了理想的修复材料。
“洞窟内的壁画和洞窟以外的画实际上作画的手法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动植物胶调和颜料进行绘制的。
那么,胶如何用到病害部位就成了难题。
起初没有经验,用毛笔往起甲部位里送胶,不是胶多流淌到表面,就是胶少黏不合。我想了不少办法,效果都不好。最后想到可否用医用注射针管来尝试做修复的工具?于是我坐着马车(当年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到距离莫高窟25医院,通过熟人找了几支旧注射器带回莫高窟。”
获得这些经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
李云鹤先生在莫高窟66窟培训年轻工作者(乔兆福拍摄)
第一次用针管做试验,也存在问题,比如:医用粗针管压力不好控制,尤其在仰面操作窟顶壁画时,不容易将黏接剂注入到起甲壁画内部,用力小,黏接剂会顺着针头往下流,用力大,又会引起起甲壁画的脱落损毁。
反反复复试验了几次,效果仍然不佳。如何能够有所突破或改进?直到有一天,李云鹤偶然看到同事的小孩手里拿着一个台式血压计的打气囊装水玩时,顿时找到了“灵感”。随后,他用糖果换来了这个打气囊,他又尝试着把医用针管的施压棒换成血压计的大气囊,极大地提高了滴灌修复的精准度和可操控性,使整个修复过程事半功倍。在日后的工作中,类似这样的“创新”数不胜数。
就是这样一支针管注射器,一剂粘合材料,李云鹤秉承一颗谦虚的心并专心致志地做实验,终究获得了突破——而这一突破的技术被沿用至今。
三、他修复的窟成为莫高窟首个自主修复的洞窟
正是有了工具、材料、技术上的革新作支撑,莫高窟抢救性保护的进程才得在窟被充分地运用,该窟也被称为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保护的“起点”。
2年8月,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所胡继高同志刚刚从波兰留学归来,行色匆匆地就随徐平羽副部长来莫高窟考察壁画保护情况。当年冬天,他受文化部派遣,到莫高窟开展壁画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的实验,研究所派李云鹤做他的助手。为此李云鹤在修复壁画的经验和技术又得以提升。
李云鹤先生在培训年轻工作者
研究所把修建于晚唐的病害最严重的窟交给李云鹤来修复。在对该窟起甲的修缮中,使用的材料是聚乙烯醇和聚醋酸乙烯混合的粘合剂,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材料。
“我一推开窟的门,瞬间感觉到空气似乎是凝冻起来的。紧接着,洞窟受到空气对流的影响,起甲的壁画就像雪花一样哗哗啦啦地坠落。”作为最早一批修复壁画的工作者,李云鹤看着窟顶和四壁及满地的壁画残片,心里说:再不修复,这些壁画就永远没有了。他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帮助它们重放光彩。
李云鹤开始了紧张而严肃的修复工作。尽管修复过程异常艰辛,但是对待这些受伤严重的壁画和塑像,他心怀悲悯情怀,耐心地做修复手术:首先是除尘。用洗耳球小心地将颜料翘起处背后的尘土和细沙吹干净,然后再用软毛笔将壁画表面的尘土清除干净;第二步是“打针”,就是将聚乙烯醇和聚醋酸乙烯混合的粘合剂,通过小号医用注射器打进已经和墙壁脱离的颜料层背部,使壁画和墙壁重新粘合在一起;第三步是回贴。待胶液被吸收后,用垫棉纸防护的木质修复刀,将起甲壁画轻轻贴回原处;最后,用较少比例的粘合剂喷洒在壁画表面;第五步是滚压,力量要刚刚好,太轻不起作用,力气大了则会把壁画粘下来,或者把颜料层压碎。
就这样,一寸又一寸,一天又一天,在李云鹤的精修细织下,一幅幅起甲、酥碱、烟熏等病害缠身的壁画;一个个缺胳膊少腿、东倒西歪的塑像,奇迹般地“起死回生”、光彩照人;
就这样,李云鹤一个人在洞窟里一呆就是多天。他修复了60多平方米的壁画,平均每天修复壁画不到0.09平方米。尽管进展缓慢,但作为全程参与抢救过窟这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修护工作者来说,研究所这座首个自主修复的洞窟就是李云鹤的功劳和心血的里程碑。
如今,窟修复至今年50多年了,保存状态良好,也没有再产生病害。
倾心尽力,只为做一件事,并且将它做好,做出名堂来,这就是一种匠人精神。
工作环境
李云鹤后来又参与了号窟,窟,53窟和94窟的壁画病害修复,也比较成功。窟湿度非常大,壁画病害最严重的起甲、酥碱和空鼓三个方面它全部都包括了;莫高窟第55窟一身菩萨周身开裂,并自行解体,被摔得粉碎。第窟北面一身天王塑身,高约3米,因为在佛坛上,后背没有联结固定的地方,大像明显向前倾斜。
李云鹤同样耐心细致为上述这些带病的壁画、雕塑“治病”:清理灰尘、注入黏合剂、用棉球滚压、再用小刀回贴压平……,扶正,垫基石,加固,塑形……。
修复工作,它绝对称得上是最考验技术和耐心的一项技术活,李云鹤却把它做得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四、国内重层壁画分离和原位整体揭取复原大面积壁画第一人
年-年,李云鹤受命到武威天梯山搬迁石窟。因这座石窟将会被水淹掉,石窟内的壁画和塑像要整体搬迁到兰州。李云鹤的任务就是负责将这些壁画和雕塑从主体墙壁上剥离下来,通过加固、装箱再跟车将它们安全运往兰州。
这座石窟的壁画剥离工作,比古代寺院和宫殿都要难,其主要原因是该壁画是依附在石头墙上,且多是重层,如果采取的措施不当,会对其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李云鹤先生在修复壁画
为了制定严谨适宜的剥离方案,就要对壁画依附的岩体进行调查。为此,李云鹤和工作组成员冒着危险,攀登悬崖危石对石窟内外进行了仔细勘测。他决定把靠近壁画的岩体凿掉,再把壁画剥离搬出。具体方案是:用壁板将壁画托住,然后在岩体上选点,再将岩石凿开使壁画与岩石分离。
这年冬天,李云鹤和他工作组成员一共八人,住在山上,吃着馒头就着甜菜叶子做的咸菜,有时还能吃到河坝挖的蕨麻烧的汤。一年的艰苦生活,他们仍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能让人感动的工匠是真正的工匠。并且认真而负责地做一件事,就会沉醉其中,丝毫不会觉得辛苦受累,这也是一种享受。
年,由李云鹤带队,对天水麦积山的两身大佛进行复位修复。两身佛像高17米,体量巨大,有上百吨。由于松鼠日积月累将松子填入佛身体内病灶处,致使大佛离开崖体60多公分。如何消除崖体坍塌对石窟造成毁灭性破坏隐患,是摆在李云鹤面前最大的难题。这个修复工作由于是高空作业,崖体高80米,修复难度异常艰辛。他们采用整体加固法对这身塑像进行了有效的修复,即:在不肢解的情况下,用锚固、捆绑固定的方法,使塑像达到复原的目的。整整三个月,成功修复。这尊大佛修复至今38年,依然完好。当时李云鹤的压力很大,如果完不成这项任务,就是千古罪人。这是李云鹤难忘且收获很大的一次经历。
李老一生对每一件被修复的作品,都有着几近严苛的完美追求。他对自己的审美是有要求的,也是有信心的,他更看重每一件文物其本身的“生命”价值。这是李老多年工作磨砺培养的性格。
李云鹤、李波父子在修复壁画工作中
莫高窟窟较为特殊,原因是在解放以前有人把表层的壁画做了毁灭性剥除,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但洞窟甬道仍保留了原有的重叠关系,因剥离壁画时的震动,其稳定性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年,研究所决定对窟甬道进行整体迁移保护。就是把宋代壁画进行了整体剥取、搬迁和复原,并续接在唐代壁画边上。李云鹤就在甬道里面做一个固定模型,支顶在壁画上,再将中间的建筑材料去除,然后将表层宋代时期的壁画向外迁移固定。这样,就可以看到暴露出的初唐、中唐、晚唐、宋等不同时期的壁画。特别是为北壁发愿文及题记为研究翟氏家族窟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李云鹤缜密研究、大胆创新与实践,使得唐宋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壁画同时展现在观者面前。这一开创性的做法,使学者研究、游客参观更为直观和生动。为此,他也成为“重层壁画分离”的首创者。
从李云鹤先生的修复工作来看,即使一个平凡的职业,也可以有自己的人生态度。所谓“器物精神”大抵如是,你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当作艺术来做,享受这份工作的乐趣,而不是为工作所累。同时,你又因为热爱这份工作,舍得在其中投入很多精力。
年至年,青海塔尔寺弥勒大殿因建筑失稳需要落架维修,同时壁画出现空鼓、断裂等病害。李云鹤应邀保护修复弥勒殿壁画和大殿建筑。病害壁画的墙体是80公分厚,壁画4米高,李云鹤没有按照常规做法剥离壁画,而是按照壁画形状做了一个模型,在没有颜色的壁画空白处打眼,把2-3公分厚的壁画固定到模板上。然后把壁画整体架立成空中楼阁一般。他又一次破天荒地采取整体剥取、原位固定、砌好墙体再平贴回位的高难度修复技法,没有任何损耗地对壁画做了成功修复,成为国内“原位整体揭取复原大面积壁画”的第一人。
青海塔尔寺验收那天,寺庙的主持活佛参加验收,他进去仔细看完壁画后问李云鹤:
“李老师,你这个壁画怎么没有给我修啊,怎么还是那个样子?”
“最想听到您这样说,我就希望这个壁画修了和没有修是一样的。损失最小的,才是最好的。”
李云鹤先生在修复壁画
这就是李云鹤先生最大的愿望,不论是谁修复的作品,都不要有明显的修复痕迹,要最大限度的保持或还原被修复品的原有文化信息,是让技艺还原艺术。而什么是“还原”呢?“还原”就是被修复好的文物,眼睛看不出修复的痕迹,这就是“还原”。
八十年代末期,青海瞿昙寺已经被剥离加固好的壁画,由于加固层石膏全部翘起来,无法复原。青海省文物局领导请李云鹤帮助做一下善后工作。当李云鹤去那一看,石膏内胶的比例太大,已经变形成锅底状,并像鱼鳞般开裂,从而加大了修复的难度。看到这种情况后,李云鹤给青海省文化厅的厅长汇报说,“我在现场没办法解决,要拿回到敦煌研究所去做实验才能得出可行性的修复结果。”鉴于文物不允许离开现场的原则,但这次破例。李云鹤将部分壁画残块带回所里研究试验。
“这个壁画的研究实在太难了。我把壁画上附加的石膏层锯成马赛克后进行剔除,然后把它们放到工作台上的一个钢化玻璃板上,一个人躺在下面看线条、人物是否吻合,一个人在上面移动调整。由于这些壁画非常脆弱,不能再生病,我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根据壁画的大小用轻质材料做了一个框子,把壁画固定住。这样,壁画无需贴上墙,反而更加结实。这个方法立即被瞿昙寺认可采用。永乐宫也采取了这个方法,但是用木头做的,现在已经受温湿度影响变形了。青海瞿昙寺的金属框架做的防腐处理,不变形。现在莫高窟洞窟,瞿昙寺,塔尔寺等等都有这种悬挂的壁画,有效地降低了载体对壁画影响的风险。”
李云鹤先生在修复文物
每一个工序都不易,每一件文物都应该被善待。这些不同年代、质地、颜色、造型的壁画和雕塑,李云鹤与它们相遇,这是一种机缘,他怎么能够轻率地对待?
甘肃天水城隍庙,敦煌南湖殿石窟搬迁,新疆库木土拉石窟壁画加固,故宫三身唐代泥塑修复……这些洞窟内不同病害的壁画或者塑像,即便是一厘米的裂缝,到李云鹤手里,都是一种机缘。正是那些残缺之美,“生病”的容颜,被李云鹤重新修复之后,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是一种心灵的愉悦。文物也能感受到李老给它治病时,对它的呵护之情与敬畏之心。
五、在文物修复一线岗位上,他85岁高龄仍然忘我工作
年,65岁的李云鹤先生退休了。时任院长樊锦诗亲自做李老的工作,请他继续为莫高窟的修复工作再奉献光和热。李老也欣然接受返聘。
返聘回来的李老工作重心不仅仍在壁画的保护和修复上,而且也更注重人才的培养上。
“六十年来,我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我现在的心愿就是报答莫高窟,报答国家,哪怕一点点也好。但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培养能通行于全国的文物保护人才。”
据李老介绍,一个大学毕业生要达到独立进行壁画修复,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而每人每天修复壁画的面积不会超过0.7平方米,靠这样的进度要完成国内数量庞大的壁画修复工作,就需要大量的人才。“正因为‘病人’太多,‘医生’太少,不能为了赶进度就不顾质量。其实,对于我们这一行来说,只有保护好文物,才能心安理得啊。”李老动情地说。
李云鹤先生在给作者写采访纪念小稿
通过李云鹤老先生培养的学生已经达到几十位,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李波,李波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26年,现在已经是研究院文物保护研究所的副教授。不久前,李老的孙子从国外留学回来,也接过了老人的衣钵。
“父亲常给我们讲:那些‘有病’的壁画和塑像和人一样,虽然它不会说话,但它知道疼。要用一颗活的心和爱的心去为它‘治病’,更要有一颗在与艺术作品相处中不断成长的心。作为晚辈又是学生,我从父亲这里深深体会到——‘匠’仅仅是一门技艺,‘心’才是修为。”李老的儿子李波对自己的父亲身怀崇拜和敬重之情,他们在工作中既是师徒又是朋友,互相欣赏,共同进步。
“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已有些力不从心,无法为莫高窟和兄弟单位抢救修复更多的文物了,但我毕生作为一名匠人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我会干到我干不动为止,我也会把自己用了几十年的工具传承给我的儿子,让他继续把优秀的敦煌壁画修复技术和匠人品质继承下去。我要求孩子们生活条件上粗茶淡饭,同志之间要与人为善,工作中间要埋头苦干。这是我的格言。”
李老笑眯眯的样子十分的亲切。谈起话来也很有节奏,笔者听起来很轻松愉悦。
在立足莫高窟保护的同时,李云鹤老先生多年来还辗转北京、浙江、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受邀参与了北京故宫、西藏布达拉宫、杭州灵隐寺、凤凰寺、新疆库木土拉石窟、青海塔尔寺、河北北岳庙、山东岱庙等30余处文物修复保护工作。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李云鹤先生在莫高窟66窟培训年轻工作者(乔兆福摄影)
如今,已85岁高龄的李云鹤仍然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壁画修复现场。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最需要他的地方。
0年,敦煌南湖店16窟和18窟文物在李云鹤的匠心独运下,两座洞窟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好无损地被整体搬迁至莫高窟北区石窟群中部塌湾;
年,李云鹤参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岳庙的修复工作,两年的时间,他以精湛的工艺将北岳庙主体建筑德宁之殿的壁画修复完成。
李老在莫高窟工作的61年里,硕果累累:修复壁画近平方米,修复复原塑像余身,其多项研究成果为国内“首创”。
《筛选修复壁画粘结剂和修复工艺》年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莫高窟窟壁画起甲修复》年获文化部一等奖、《莫高窟窟重层甬道壁画整体搬迁与复原》年获文化部四等奖、《敦煌壁画颜料X光谱分析及木结构建筑涂料》年获文化部一等奖、《莫高窟大气环境质量与壁画保护研究》年获甘肃省环境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敦煌莫高窟环境及壁画保护研究》年获国家文物局三等奖、河北曲阳北岳庙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年获得全国第三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十佳工程。
作者陈旻采访李云鹤先生
就在一个仿佛远离尘世的、弥漫着古代和异域气氛的榆林窟第15窟这个始建于中唐,后经过宋、西夏、元修改的洞窟里,李云鹤老先生面对南壁中部“赴会菩萨”腿部面积有两寸大小的“起甲”壁画,进行清理灰尘、注入黏合剂、用棉球滚压、再用小刀回贴压平。整个过程大约二十分钟。
面对这一整套工序,笔者和李老的两名年轻学生几乎是屏息静气地看完。
李云鹤老先生在修复这上千年前的艺术作品过程中,他仿佛是游走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中,也游走在古代匠人和现代匠人的对话里。虽然,他与古代匠人无法真正交流,但是,当李老把这些病害的壁画修复完成后,起身离开,他就已经与古人经历了一场十分精彩的对话……。
作者简介
陈旻自由撰稿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中国环境报》特约撰稿人。《当代敦煌》采编、专栏作者。图书《马王巴拉图苏和》作者,作品《秘境阿尔金山》入选中国生态文学优秀作品集《大地文心》。作品见于《中国环境报》、《映像》(中国最美期刊)、《中华英才》、《环境经济》(中国环保核心期刊)、《中国摄影报》等报刊杂志。
个人事迹被《中国妇女》(外文版)、《中国女性》、《远方的家》、《映像》(中国最美期刊)、《妇女之友》等媒体报道。
作者往期文章点击推荐
百年文杰:用百年修行守护莫高千年“魂”
杜永卫:用信仰雕塑的别样人生
面壁佛窟传绝技——赵俊荣的敦煌临摹世界
高山:“出世”的画家,“入世”的道人
孙洪才:穿越千年的色彩轮回
边振国:让生命在线条中游走
陈竹松:腹有诗书气自华
罗布泊|公里极致穿越,发现神秘历史遗存
霍熙亮
三生缘起莫高窟
孙儒僩
潜心深山佛窟一生守望敦煌
张仲
九十岁的敦煌“活字典”
本期编辑:远近贲守梅
封面设计:贲守梅
-END-
投稿信箱:
m
.福州白癜风医院沈阳白癜风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