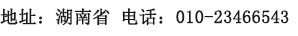归去来兮
娄光
娄光,原名娄法矩,字成方,笔名小兀、齐清园。年出生,山东莱州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海燕》发表了处女作《门风》;其后在《小说月刊》、《短篇小说》、《海燕》、《山东文学》、《胶东文学》、《雨花》、《北方文学》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多万字,在《知音》、《女报》等杂志发表了大量纪实作品。其中小说《大火》被《小说月报》选载;《家事》被《微型小说选刊》选载;《少年少年》被《儿童文学选刊》选载并获《少年文艺》创作奖,《乡村郎中》获《当代小说》征文优秀作品奖并被《短篇小说选刊版》选载,《大火》、《空间》获烟台市文艺创作三等奖。年赴青岛经商,年春再次写作。仿佛是刻意的安排,他行李一卷,没有任何理由和征兆就回家来了。当他拖着拉杆箱走在桑梓路上时,街坊邻居,远亲朋友,根本不相信,一个走惯了的人,自由惯了的人,又是一个小伙子,会安心住回短短的桑梓路?他们都想,他肯定会走,迟早的事。人们都在疑惑,他接到了娘的电话,娘病了,他的心一凉,但是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是该回来的时候了,在回来前他似乎已经听到了娘的召唤。
他迫不及待地来到娘的面前,天上掉下来一般,娘惊呆了,死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他苦笑了一下,我回来了,不走了。
你---能不走了?连娘都不相信他的话。
娘的质疑自有她的道理,以前家里出现那么多事他都没有回来,现在能无缘无故的回到桑梓路?笨手笨脚未婚的儿子能回来照顾她?他有一份自由工作,在网上给人画像谋生。根据买家提供的照片来作画,无论男女老少,只要给钱,他就画。也接过几单特殊的,给死后毁容者画面具,罩在死去的肉体上,以安慰一切值得安慰的。至今仍记得第一单,死者是个女孩,十六岁,车祸,面目全非。非到什么程度他不知道。家属提供了女孩的生前照片,含泪请求他复原花季少女的容颜。他花了几天时间,终于让他们满意。
这只是工作,收入还不菲,他没有理由不坚持。其实,在哪儿生活都一样,既然故乡与异乡常处于置换状态,此地与彼地也只是外部环境,那一切都是无关紧要———他越来越住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以前他也无数次为自己寻找回家的理由,他和父母没有隔阂,和家里任何人都没有过节,更不用说仇恨,可是他说服不了他自己,他已经习惯了孤独的漂泊,习惯了那样的生活方式,孤独宁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许这也是一种时代的方式。他总是想,还有娘呢,一切都不晚。娘一直喊他回家,喊他结婚生子,过安稳日子。他就是不回来,听也不愿听,虽为母子,却是两条心,不可能沟通,也不想沟通。他不觉得这是什么遗憾,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听另一个人的,哪怕是母子。他也没有理由重复娘的人生。
现在,他回来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来,总之,他回来了。他听从了心里某个声音的召唤。在心理上仿佛到了非回来不可的地步。现在,他必须照顾好娘,再照顾好生意,让日常运作下去就好了。照顾娘比较麻烦,这件事想起来他曾非常胆怯,病人多性子,何况娘又挑剔,再说又他不是发自内心,完全是责任,这就得费点心。可是,没有理由逃脱,他要学会做饭,还有学会耐心,有了耐心坚持下去就可以了,总有解脱的一天。这么多年,他知道自己从没有真正思念过亲人,说出来怕被人耻笑,或许时代的自由开放已把他塑造得非常冷漠,再因为,一个人在外面的日子太自在,太舒服,越跑越远,还想跑得更远,一直没有找到回家的理由。一晃几年过去了,家里,祖父母早走了,爹也走了,小动物都死两代了,只剩下娘了。就在这个时刻,他突然觉得不能让自己等他们都死绝了,才跑到坟前痛哭。
生活重复起来。他根据娘的病情在实践中制定了菜谱,还专门买了血压计,学会了量血压,测血糖。他们每天的日子是这样开始的:他先起床,准备好早饭后,叫娘起来。餐前测量血糖,记录在册,开始早饭,定量供应,不多不少。饭后,他赶娘出门锻炼,随身携带糖果饼干和急救卡。一小时后,娘平安返回。娘每回必叫,饿死我了!他给娘蒸南瓜。南瓜很甜,不是放了糖的那种甜,娘吃得狼吞虎咽。其实这样的日子对于一个未婚男子来说,不管从心理上还是从生活上都非常困难,但是他必须做,以前是娘做饭给他吃,现在他必须掌握这些生活技能,娘老了,病了,是需要他的时候了,为了做好饭,他买来了食谱和菜谱,慢慢学习着做以前陌生的生活。
吃完后,娘总说,再量一量血糖吧。娘喜欢吃,但又怕吃多了会血糖高。血糖一高,头就会晕。一旦头晕就很容易出事情。可是,南瓜没事。神农尝百草一样,他给娘吃过很多东西,什么鸡蛋饼、红薯、土豆,一样样遍尝,惟独南瓜没事。南瓜是娘的宝。
他在画布上画南瓜。娘看到草丛里滚出一个圆溜溜的黄球,问他,这是什么啊?他答,当然是南瓜啊。
娘叹口气说,又是南瓜啊。
娘,你就认命吧,没有比南瓜更适合您了,毕竟它是甜的。他在心里说。书上说,南瓜含钴,钴能活跃人体新陈代谢,参与体内维生素B12的合成。钴还是人体胰岛细胞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对防治糖尿病和降低血糖有特殊疗效。
娘得的是糖尿病,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后遗症了。比方说眼睛开始有些模糊,邻居们却说这是富贵病,比起肺病、肝病什么的,娘应该知足了。再说,这病除了忌口,暂时没有什么危险性,当然这是暂时的。有些后果,他不和娘说,说了也没用。灯下,娘絮絮叨叨,我可比你爹好多了,他是活活疼死的,而我呢,得的是居然是富贵病,呵呵,笑死我了。我这样一个人,可有什么富贵可言?
娘忽然不说话了。大概他想到了做姑娘时村庄里有个人叫富贵的,后来做了乞丐。做乞丐的叫这个名字?类似于辛苦一辈子的穷人得了富贵病?说的就是她自己呢。
想到这里娘再次笑得不行。娘严肃了一辈子,临老了,倒有了些幽默感。为了安慰娘,他告诉娘,整个中国得这病的人,快要一个亿了,就是说,每十三人中就有一个生这病。
娘说,他们都要饿着肚子吗?
当然,想活命的人都不会让自己吃得撑死。
娘又说,那我以后也少吃点吧。
他点点头。
娘很寂寞,自从爹死后,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世上活。这也没什么,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照样活得好好的。只要控制好血糖,而不是明白人生的意义,娘就能活下去。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娘活得久一些。这是他的责任。
回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有人喜欢娘,那个人就是隔壁的鳏夫,五十上下,死了老婆,隔三差五来家里给娘送吃的,有时候是自己钓的一条鱼,有时候则是一袋时鲜水果,说是乡下亲戚送来的。娘也把家里吃不完的东西回赠他。有一次,两个人在客厅里看电视,嗑瓜子,说说笑笑的。当看到他从画室里出来,马上不笑了。他隐隐地闻到了一股扎啤的清香。他侧了侧头,看到茶几上有一只空杯。
那男人慌慌地站起来,我——是我喝的。
短短的桑梓路上扎啤屋一个接着一个,这里的人都喜欢喝扎啤,自然也包括娘。
他没有看那男人,也不吱声。
娘尴尬地站起来说,这是你二叔。娘的手指指着那个男人,眼睛却看着别的地方。
他依然没有吭声。
娘没有像小时候那样强迫他叫人。男人讷讷的,似笑非笑。
他继续站在门厅里,打量着那老男人。那个人,脑袋前半部分全秃了,后面半圈隐约有些生机,蓄着一撮小胡子,嘴唇倒比有些女人还薄。最讨厌留胡子的男人,他暗自嘀咕着。
男人踮着脚出去了,娘也把电视机关了,眼睛看着窗外出神。
他对娘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吗?
娘摇头。
因为人不干净,女人也不干净,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更不干净。他既然知道你有病,还带扎啤来——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就想这么说,说给娘听。
真的—--是他喝的。娘怯怯地有些愕然,此后好久没有说话。
娘不高兴了。有一天,趁他外出买颜料,偷了他的钱去街上逛。包子馒头葱油蛋饼鸡蛋卷,哎呀,街上好吃的怎么那么多,喜欢什么,买什么,平时不能吃的、节制着吃的,此刻大快朵颐,无须克制。当然也喝了扎啤。吃得过了,走不动了,想去公园里逛逛,消耗一下,晕倒在绿地上,医院,才拣回一条命。
后来娘回忆说,她捧着肚子在路上走时,只觉头越来越晕,视线越来越模糊,脑袋越来越沉,抬头一看,太阳挂在树梢上,像个烧焦的黑南瓜。她心里一急,呀,不好,要出事了,还没来得及打电话,就晕倒在地。
从此之后,娘变得小心翼翼,再不敢使性子。她说,要死的时候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其实,她想说的是要晕倒的时候。
以后,每次吃饭,娘总乖乖地吃分她的那份。再想也不提扎啤两字。迅速吃完后,搁下筷子看他吃。娘总说,别急,慢慢吃,我总算想明白了,人没必要吃那么多,不饿死就行了。
他为娘的见解吃惊。
娘又说:吃了还得拉出来,相当于白吃,多吃多拉,少吃少拉,没意思,人活着也没意思的很。
娘这样说,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知道娘不过是说说而已,其实还是喜欢吃。
生病前,娘的胃口好得不得了,具体饭量无法估计,没有小菜佐饭,也能吃下好几碗米饭、面条。娘说,小时候,家里穷,一大锅子饭,一点点菜,咸菜,咸鱼,咸酱,只要是菜必是咸的,用筷子蘸一蘸,就能吃下一碗饭。
晚饭过后,洗了碗,刷了锅,娘望着他,有些无奈地说,让一个男孩子做这些事,也真是难为你了。他无言地笑,谁让你只生了我一个儿子哪?!
家务完毕后,两人灯下对坐。他心不在焉,脑子里回放着过往生活的片段。娘则东拉西扯,他嗯嗯呀呀,给予响应,其实不知所云。娘也不在意。因为,娘在回忆,回忆那点与吃有关的事儿。常常是,说着说着,娘嘴里吧唧吧唧,表情古怪,梦游兮兮的。娘的馋病犯了,蛔虫在肚子里打滚。
既然不能吃,说说也好,说到这些娘也会想到街上新鲜的扎啤,就让娘望梅止渴一下吧。
这天,娘说的是炒猪肝。那还是我小时候的事,腊月二十二了,杀猪的日子到了,一大早,黑还没亮透,杀猪匠扛着木桶子,穿着胶鞋,哐当哐当进院子来了,我娘在烧水,锅里的水烧得滚烫滚烫,猪被绑在杀猪凳上,哇哇乱叫,一刀扎下去,脖子里的血泡泡突突冒个不停,很快它就不动了,然后,它的肚子被剖开了,板油白花花的,我们全家围在边上,连猪肚子里的粪便都香喷喷的……。说到这里,娘咽了咽口水。
娘说到猪粪,让他想到猪肠子以及那里面的东西,这让他感到恶心。
你不知道那时候的猪肉有多香……。娘继续说道,嘴里吧唧吧唧,双眸神采奕奕,好像饿死鬼闻到了肉香。
我不喜欢吃肥肉。他轻轻嘀咕了句。
那你不懂,肥肉才香呢,半肥半瘦最好,放在油里一煸再一焖,味道就来了,当然最香的是猪肝,猪肝炒大蒜,咬上去,沙沙沙,连牙齿都要唱歌了。此时,他才想起医嘱:糖尿病人忌食动物内脏。娘已经有半年未食猪肝了。
你记得不,小时候你也很喜欢吃蒜苗炒猪肝的。娘又加了一句。
他摇了摇头,不记得了。他对吃的东西都没有记性,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特别想吃的。如果临终的床榻上,有人问这个问题,他多半是要摇头的。
不是说他尝尽了山珍海味,应该说,他吃的不会比别人好多少,相反倒要粗糙得多。如果真要让他说出一样,他脑子里浮现的是那年冬夜,他刚到那个城市,好不容易找到夜间兼职,下班后饥肠辘辘回租房,没钱吃夜宵,同租房的女孩分他一包泡面,那香味让他终身难忘。
难以忘怀的美食竟然是泡面?他从没有对人说过这些,自然不能和娘说。娘会心疼他,以为他在外面很苦。其实不是这样的。
娘和他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娘经历过饥荒,他们那一代人,为了活命,什么东西都吃过,树皮,草根,野菜。就因为如此,他们重视吃,就怕没东西吃。这顿吃了还不够,还喜欢藏着,备着,这样才有安全感。
他想,那真是吃的黄金岁月啊,人人争相觅食,满大街的狗也在找吃的,个个食欲惊人,好像宇宙黑洞藏在每个人的肚腹里,怎么也填不满,怎么也吃不饱,越是吃不饱,就越想吃。饿昏了的,眼冒金星的,四肢无力的,看到人都想咬一口。其实已经没有力气咬了。
说起来,他们这代人,倒是生命力不够旺盛,做什么事情都是恹恹的,没有食欲,没有上进心,他们的欲望在别处,在毫不相干的地方。
他有时候也想让娘吃个痛快,人生在世,多不容易。如果生这病的是自己,他绝不会为难自己。他照着食谱给娘做好吃的。娘的食欲更加被勾出来了,就像饥饿的狗闻到了肉香,抓狂不已。
这是茄子啊?怎么有肉味?你烧的是肉吧?娘用筷子敲着眼前的这道油焖茄子。
他笑了笑,说:娘你尽管吃吧,没有放肉呢。
娘睁大眼睛,不相信似地看了他一眼,又说:很香哪,那你以后多给我做点这样的菜吧,比饭店里烧的还好吃。
娘吃完了,举着筷子,吃惊得不行,神情讷讷的,似乎还停留在对美味的回忆中。
他想起小时候娘烧的菜,青菜炒得发黄,茄子是隔水蒸出来的,大白菜是水煮的,无色无味,只是熟了而已。那时家里条件已经不错了,可娘一点做饭的天赋都没有,从没觉得做饭还要学,不是烧熟就能吃的东西吗?他怀疑自己食欲欠佳,与小时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有关。这倒让他的欲望,完全转移到别处去了,比如他一直在外面浪走,因为在吃食上从不挑剔,倒很快就适应了浪子的生活。
娘不想天天吃南瓜。娘说,外面在卖一种草药茶,吃了能降血糖,彻底治愈糖尿病,大家都在排队呢,喇叭在叫,可能很快就要卖完了。娘说,一个月三百块,吃三个月就好了,也不贵啊。他说那是骗人的,是忽悠老年人的,你怎么能信这些?娘说,就九百块钱的事,你怎么就不肯?他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们在骗人,专门骗老年人,这种江湖骗子,我见多了。
娘又说,很多人都去买了,连降糖药都停了,就吃这个了。
他说,一帮蠢人,他们会后悔的。娘瞪着他,很久不说话。她张了张嘴巴,又闭上。他没说,这世上还没有一种药是能治好糖尿病。如果病都能治好,那还叫病吗?
娘到底做了出格的事情,千叮万嘱,不能吃糖,不能吃糖,娘还是偷吃了糖。是邻居孩子结婚时送来的两包喜糖,放在橱里差不多忘了,里面有大白兔、阿尔卑斯、德芙,玉米软糖,水果硬糖,芝麻花生糖,花花绿绿的。娘悉数吃下,把糖纸扔炉灶里烧了。不仅是糖,还有奶油饼干、蜜饯、瓜子,家里的零嘴,有益无益,都被她吃个精光。吃完后,娘坐在床边发愣,后来头晕得厉害,昏昏沉沉躺在被褥上,连衣服也没脱。
当他发现后,吓坏了,一测血糖,二十好几,赶紧叫了救护车。
那次,他和娘大吵。
你就那么不想活命,我这么大老远回来,可为了什么?要不,你想吃吃什么,想喝喝什么,我什么也不管了,怎么样啊?
娘不说话。
活着重要,还是吃东西重要?又不是不让你吃,叫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还以为我舍不得给你买?你是我娘呀,能吃我还不让你吃吗?
娘想了想,说:你别生气,我还是想买那个草药茶,吃好了,你就不用在家照顾我了。你不是还有自己的事业吗?
他一惊,原来娘这样想,以为这病能好,好了之后,再赶他走?
他给娘买来那个茶,是粉末,每天三次,每次一包,冲着喝。卖药的说,连吃三个月,包好。他问,如果不好怎么办?
不好?这怎么可能,包好,包好。骗子是一群人,团队合作,还有托。买的人确实很多,都是和娘一样的老人。他想,这么多人在买,就当是安慰剂吧。
他拎着药回家了,一个绿色方形纸盒子,画着翠绿的草叶,娘见了,如见圣物,从他手里恭恭敬敬接过,小心翼翼打开。
这茶真香呢,有股药香……娘边喝边赞。
他没多说,只想,但愿没什么非法添加剂。
自从吃了它后,娘的精神大好,对他说,头不晕了,眼也不花了,动作利索多了。他怀疑这是心理作用,也不道破,只求他不得停服二甲双胍。
娘还算听话,药茶照喝,降糖药照吃,娘也怕死哩。
有一天,娘说,这药真的好,你二叔也在喝!
娘说完就捂了嘴。
他故装没听见,笑了笑,说,你先吃着,如果真的好,吃完了还给你买。
娘慢腾腾地说,你二叔其实不错,你爹走后,多亏了他照顾。
他说,娘,您放心,我会照顾你后半辈子。
他不敢看娘的眼睛。
娘叹了口气,去房里看电视了。娘除了看电视、吃药、量血糖,别的事情都插不上手了。
他把娘像佛一样供起来。这样挺好的。
他们每天的生活基本如此,很少变化。娘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后遗症越来越重,眼神儿越来越模糊,腿肿得抬不起来,心脏也出现了问题,老是感到胸闷。
他越来越不放心娘一个人出去,就让他在屋子里绕绕圈圈,踢踢腿,或者看电视。他通常在房间里处理网上生意,有时候画画,抽空去菜场买菜。除了必不可少的,他们不太说话,他很忙,根本没有时间说话。有时候,他透过画室的门缝看娘靠在沙发上,腿搁在茶几上,电视屏幕一闪一闪的,已经调低了声音。娘天天看默片,看着看着,会睡着,醒来继续看。
给死者画面具是他网店里的特色,也不是什么活都敢接,要先看照片的,看了再作决定。有些脸让他喘不过气来,极美或极丑的,他都没有力量画下去。只有那些平淡的,毫无特色的,温和的脸,他才肯答应下来,并在面具上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这样的作品,通常能让家属满意。因为,他把它们画美了,画“仙”了,画得不像这个世界的人了,是对原有容貌的升华。人们比较容易接受美的事物,哪怕不真实。
他从不和娘说自己的这一部分“职业”,怕她忌讳,娘是那种见了寿衣店都要绕道的人。
他起先完全是看在钱的份上,承揽了这类业务。它们比画一张普通作品的报酬要多上三倍。但画着画着,倒有些迷住了,好像是重新创造了一张脸,一张没有黄褐斑、皱纹和庸俗表情的脸,一张很“仙”的脸。自从30岁之后,他对自己的脸、别人的脸都多了
一天,他接到离奇的一单,一个女孩因不满自己的容貌自杀死了。悲痛欲绝的父母,找到了他,要求他画一张与女孩的心灵相媲美的脸,满足他生前无法实现的梦想。而唯一的线索是女孩的日记。女孩有很好的文采,早熟,忧郁,对哲学早有介入,他的自杀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或许不排除爱而无果的可能。女孩懂得太多了,这让她比常人更渴望得到爱,而平庸的容貌又阻止了这一切。她没有朋友,没有初恋,甚至父母也是事后才明白女孩的价值。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注定是个异数,她太痛苦,太强大了,把一切都考虑到了,所以选择了死。
他注意到女孩喜欢的作家中有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人的名字。女孩还喜欢樱花,尽管从未见过那种缤纷而短命的花瓣,但她的喜欢不是盲从。
女孩甚至跑到乡下的外婆家生活了一年,对自然作了一年的观察记录,女孩在日记中流露了对这那个荒僻世界的深情。他把这个看成女孩对世界的告白。果然,女孩的最后一篇日记在对乡村废弃池塘的描写中戛然而止。
拜女孩父母所托,他开始构思女孩的容颜,至此才发现所有现存的色彩根本不够用,连画几稿悉数被毁。当所有的形象一旦固定下来,就显得庸俗不堪。他企图进入女孩的内心寻找,依然一无所获。他想,内心的东西根本无法在外表上显现,所以,外表和内心分离是对的。所以女孩没有绝美的容颜也是对的。
在女孩双亲的催促下,他研究了世面上所有流行的大小女星的脸,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叫伊能静的女星的脸,稍作改变,他画它在面具上。如果非要画得美,只能这样了。
女孩的双亲感到完全满意,对他感激涕零,在聊天记录上留下许多感激的话,代远在天国的女儿向他致谢。他不知道与他聊天的是女孩的父亲还是母亲。这个人打字速度很慢,不知是悲伤,还是不习惯使用计算机。
事情过去两个月后,他们又找到他了。要求他重做一张女儿的面具。
为什么?
我们想念她。
家里不是有照片吗?
就给我们再画一张吧。
他答应了。他想象那个面具挂在这对中年夫妇的卧室里,时间久了,女孩的母亲或许还会想,我怀她的时候,梦见的就是这张脸。
这个画面不时折射到他的脑子里。一会儿,他把那张脸换成娘的,娘成了如花的少女,挂在他卧室的墙上。
有一天,饭桌上,他忽然和娘说起那些老照片。那时候,娘的下肢已经出现中度浮肿,一压一个印子,这是典型的糖尿病后遗症。他暗自惊惶,心想,有些东西看来真的会来,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娘说,什么照片?
他说,你年轻的时候,在外婆家的园子里,胸前垂着两条辫子,穿着花裙子的那张……
娘说,我不记得了。
他说,你再想想,真有那张照片,我小时候见过的。
娘说,真的不记得了,你要那些旧东西干什么?
他说,我有用。
过了一会儿,娘忽然说,照片丢了就丢了,什么时候你给我画一幅吧。
他顿了顿,支支吾吾地说,你把那张照片找出来,照着照片画,好画,省力。」
娘却说,照片哪有本人真实啊。
我怕你坐不住,要一动不动坐上半天,才能画。他解释说。
不怕,我坐得住。娘非常干脆。
那好吧,只是,最近比较忙,等空了再说吧。那声音有些轻,连自己都听不清。他胡乱扒着饭,不敢看娘的眼睛。心里仍想着那张旧照片,娘蹲在花树下,两根辫子垂在胸前,眯着眼睛,说不出的温柔。他想象那个夏天,园子里的花能开的都开了,有夹竹桃,石榴,鸡冠花,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阳光很强烈,晒得篱笆滚烫,整个世界昏昏欲睡。娘蹲在花树下,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她看着自己的碎花布鞋……
他只想画那时候的娘。
慢慢地,该来的都要来。他以为自己做足了准备。可是当真的来了,还是手足无措。
那天黄昏,娘在阳台上晾衣服,忽然,命运的邪恶之手,将她向后一推,再一推,娘的右脚被矮凳绊倒了,一屁股摔坐在地,爬不起来。娘疼得呲牙咧嘴。从画室里跑出来,看娘摔倒在地的那一刻,他异常平静。医生的诊断结果是,髋骨骨裂,建议静养三个月。当娘的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解决时,他感到娘真的开始需要他了。他回报的时候到了。
每天天未亮,他就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到娘的房间里来,伺候她排掉夜尿。娘很重,要让她肥硕的臀部架在尿盆上并非易事。当终于摆布成功,娘急急地排尿,他听到那嘘嘘的排尿声,就一阵反胃。当端着尿盆去卫生间时,他马上闻到一股怪味道。当他准备早饭、伺候娘穿衣,给娘喂饭,一样样做过来时,那味道越来越重,越来越难闻,刺得他呼吸困难起来。
他开始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打扫卫生,里里外外,又是拖地板,又是擦桌椅抹柜子,经过一番清洁,那味道总算消了些。
他打扫的重点是:娘的床底及周围空间。只要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稍稍长一些,打扫得认真一些,娘就以呻吟声来抗议。
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障碍,在做这一切时,他尽力忘却性别,可娘并不自然,在他的面前还躲躲闪闪的,不时还满面羞涩地说一句,你要是个女儿该多好?他故意黑下脸来,我是你儿子,你怕啥?不是,儿子也有不方便的呀,娘说。那你为什么不再生个女儿?他故作轻松。唉!娘长长地叹气。
每当娘发出哼哼的声音,他就停下手中的工作,关切地问道,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娘通常说,快扶我坐起来,我的腰快断了。
一旦娘坐起来,嘴巴一张,他马上就去打开电视机,不然娘就要没完没了地说开了。娘抱怨自己的腰,自己的腿,自己这把老骨头,一动不能动,比死还难受。
娘一说话,他就把遥控器递给他,然后退出房间。紧接着,娘的声音就被电视里的人声给淹没了。
娘有段时间没擦身了,皮肤上长了一层白糊糊的类似鳞片的东西,一撩衣服,尘粒一样,纷纷坠落,有股要吃到嘴里去的恶心感。他最害怕这个。
印象中,他没有见过娘的身体。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自己洗澡。因为是儿子,他对娘的身体是陌生的。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象,当在公共场所看到那些中年女人的身体时,那种念头曾一闪而逝。现在,他要为娘脱去衣服,擦拭身体。娘面色极其尴尬,望着他,低声说,我还是自己洗吧。
他也尴尬地笑,但面色故作轻松,还是来吧。
要不就不擦了?娘几乎是用祈求的目光望着他。
自己的儿子你怕什么?其实他巴不得不擦,可是在娘的面前必须克服一切障碍。当他给娘解开衣服的第一颗扣子时,心几乎要跳了出来,手也抖得抓不住纽扣。
他咬牙做了下去。努力把娘的身体想象成一件陌生的物体。
当娘的身体完全暴露在他的视野里,他只想夺路而逃。羞耻?惭愧?震惊?现在他必须面对,只能中性地面对娘的身体,忘却男人女人,他是儿子,他不知道娘已经这么老了,老得皮肤起皱了,毛发变白,比外面看上去老多了。没有肉的地方,骨头棱棱。有脂肪堆积的地方,一摸是一处松软的沙堆,绵软而无力。
娘在尴尬中忍受,可她已经无能为力,身不由己。他每做完这事,就逃也似的奔出娘的房间,把头埋在棉被里,喘息不已。而娘在他离开的那一刻总在低低的哭泣。早知道是这样哪该生个女儿!娘总是这样说。都是自己的孩子,还不一样吗!他故作轻松。下次,打来水,拧干毛巾,把窗帘拉上,把娘的衣服一一脱下,他的震颤感又出现了。好像一个老年男人打量着年老色衰的情人的身体,完全地崩溃了。除了给娘擦身,其它的,他都慢慢适应过来了。包括端屎倒尿,那股子恶臭,他都忍了,这是娘,她曾经给他做的,现在必须要一一回报于她。他想过,如果他是女儿,女人对女人的感觉或许更糟,对于娘,在这种心态下,儿子和女儿的感觉或许没有区别。娘所渴望的仅仅是性别上的顺从和安慰。
这期间,二叔来过娘房间几次,他都回避了,给了他们单独说话的时间。有时候二叔在娘的房间里会坐上半天,他们的声音被电视机的声音淹没了。娘在二叔来过之后,心情会好上一阵,食欲也有所好转。他再也不用担心娘旺盛的食欲了,因为她几乎吃不下什么东西了。整天躺在床上,消耗也少,娘变得萎靡不振,他又想着法子让娘多吃。娘却怎么也不肯多食了,还说,吃得多,拉得也多,太麻烦了,没意思。他不知道如何说服娘,如果那个躺在床上的人换作自己,多半也会这么想。他们都是不愿麻烦别人的人。可他要回报娘啊,这是他唯一和最后的机会,如果错过,将后悔一辈子。
有一次,他刚给娘擦过身,房间也打扫过了,二叔来了。他拎着一篮子水果,他瞄了一眼,里面有苹果、樱桃、荔枝、蟠桃等,每样几种。娘不能多吃,但每样尝一点却是可以的。
他笑着说,二叔的心真细呢,还请二叔多劝劝娘,让她多吃点,她现在是吃得太少了,营养跟不上了。二叔也笑了笑,径直进了娘的房间。他在后面看他的秃顶,回想他的蒜鼻子、薄嘴唇,忽然有了异样感。人家没有义务经常来看娘,娘是病人,病人身上是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再说,娘已经老了,可能连时间也不多了,他图什么?
他看到二叔进了娘的房间,就干脆出了门,决定去街上溜溜。他好久没有买衣服了,可是他却走进了一家女装店,一下子买下好几件。他都给娘买的,松松垮垮的那种,亚麻料子,墨绿色,上面有红色暗花,适合当睡衣穿。他想,如果娘不喜欢,自己再来换,或者送给二叔的家人。
他没想到,娘对这件袍子一样的衣服非常喜欢,一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叫他给她换上。他看到娘穿新衣服的高兴样,才发觉自己从没有给她买过衣服。娘很高兴,你这傻小子,眼光比女孩还好。以前在外地,都是寄钱给她,生日、节假日,他能做的只是寄钱。他不知道娘喜欢什么样的衣服,以为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到。
有一天早晨,当他推开娘的房间,猛然发现娘穿戴整齐,坐在床上。娘穿的是那天他买的衣服,宽大的墨绿袍子,遮住了她的大半条腿。娘坐在床沿边,安静地看着他进门。娘清清爽爽,连头发也梳过了,根本不像病人。
你看,我这样穿,怎么样?晨光中,娘的声音微弱却异常坚定。
他点点头,眼神游移在那件墨绿衣服的边上,飘飘忽忽,始终没有落到实处。他不敢看娘。娘是从来不说衣服好看不好看的话,她是那种漂亮衣服不爱穿,专拣大众化的来穿,就怕自己惹人注意。
娘说:你画得不错,小时候,你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吵着要去学画,你爹说画画烧钱,但我们都不后悔让你去学这个,你看,你现在都能在家里上班养活自己了。
他点点头,说,爹说的没错。过了一会儿,又说,谢谢你们让我学画。娘不语,笑了笑,说,要不,你什么时候也给我画上一张吧,就穿这身,我靠在床上,你慢慢画。
他一怔,以为娘已经忘了那事。
本来,他想说,我不会画,怕画不像,可他看着娘的眼睛,这回,他终于接过了娘的眼神。他听见自己轻轻地回答了娘。有一个声音在说,好的哦。
那天清晨,他感到浑身虚脱,好似多年来层层蒙住的面纱,猛地被人揭开了。他想,是时候了,该有个交代了,这么多年的母子,再这样回避下去,说不过去。心里却痛苦极了。他看见娘点了点头,缓缓躺回被褥上,松了口气。
这之后,他如往常那样进出娘的房间,给他喂饭、擦身、端屎倒尿,如进入神圣的仪式当中,毫无不耐烦之感。他在照顾自己的母亲,已经习惯,只愿这个过程延长再延长,以消除心底淤积多年的心事。他努力寻找给娘作画的灵感,这必然是他此生最重要的作品。
有一次,当他扛着画架来到娘的房间门口,却痛苦地站住了。他远远没有准备好,对娘似乎无需熟悉,却又充满陌路感。他不知道如何激发心底的创作欲,在那短暂而浩瀚的时间,调动所有的前尘往事,足以让他崩溃。白日时,他多次趁娘入睡后悄悄潜入房间。坐在昏暗的光线里,听娘的呼吸声,娘的喉咙里不时发出呼噜音,时轻时重。人越老,呼吸系统越不好,越容易发出声音,娘就是这样。恍惚中,他以为床上睡的是爹,家里只有爹才会在入睡时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却从不敢走近细瞧娘的神情,怕惊醒她。他觉得娘是能随时醒来的。
有一天午后,趁着娘入睡时,他蹑手蹑脚进入,轻轻拉开窗帘,让阳光进来,照在娘脸上,支起画架,拿笔的手在颤抖。想象中的刷刷声迟迟未来。他根本无法下笔,眼前这个人所引起的震颤感阻止了他进一步的举动。当他以全副精力来观察娘,那个他所观察的人,却给了他剧烈的陌生感。这个熟睡的老太太似乎根本不是娘,而是另一个与他无关的人。他努力接受娘的新形象,并从这个形象中得到启示。
娘并不美,年轻的时候没有美过,老了更无风度风采可言,与身边的老人没什么两样。黑而瘦小,满脸老人斑,皮肤皱得不成样子了,看人的眼神是空洞的,除了食物,对任何事物都无兴趣。现在,娘对食物也没了热情。他甚至觉得这是一个玩笑,像他这样四处浪走、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怎能有一个如此庸俗的娘?
他无数次想过娘死的样子。一条被子遮住了娘的半张脸,没有睫毛的眼睛紧闭着,嘴唇微微张开,一切安然,没有挣扎的迹象,已经停止了呼吸。娘通过睡眠进入另一世界。
这也是将来他死时的场景。所不同的是,娘的死由他来发现,处置,掩埋。而他呢?或许要由别人来发现、处置、掩埋,可那个人与他毫无关系。说起来,他比娘的命运更凄惨。可他并不这样觉得。
其实,他选择回来,就是为了等这一天。娘死的那一天。
娘的腿疾越来越厉害了,红肿而黑,橡皮一样粗,根本抬不起来,不知里面蓄了多少毒。身上已经很瘦很瘦了,惟脸蛋勉强有点先前的轮廓。血糖的测量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和娘都回避了当初那么重要的事。
他问娘喜欢什么,只管吃。他不敢说的那么明,病人都是多心的。但娘什么也没说,娘什么都知道。
那天上午,伺候娘排尿、进食之后,他又这么问了。娘想了想,说出两个字:桃子。
五月果然是有桃子了。他很高兴领了圣旨在街上奔跑,找了好几家水果铺,都嫌不够新鲜,很巧地碰见一个中年男人担着半箩筐在街上叫卖,桃子哟,卖桃子哟!新鲜的桃子哟!他捧着桃子跑回家,想让娘看看这些桃子是多么新鲜!上面还有微微的绒毛,就像很久以前吃过的。
小时候,娘从集市回来,从新买的塑料痰盂里掏出一把桃子塞给他。他怎么也不肯吃。娘说,干净的呀,吃吧,很甜的。
他始终嫌弃那桃子是在痰盂里装过的。尽管装桃子的痰盂是新买的,可它毕竟是痰盂呀。
他捧着洗净的桃子一边推门,一边叫着,娘,桃子来了。娘没有答应。他推开门,电视里正放着一部间谍片,一个女人正举着手枪瞄准黑暗中的敌人。娘坐靠在床头,脑袋歪在一侧。他感到奇怪。娘睡着了么?说过几次了,这样睡觉会脖子疼。他加快步子走去,走近了,看清楚了,还是不敢相信,连哭都忘了。
他把娘的身体摊平,把枕头也放平,重新帮娘盖好被子,只让娘露出脸来,桃子盛在白碗里,放在娘的枕边。那气味依然新鲜。顿了数秒钟,他走过去拉开窗帘,阳光哗地一下,全进来了。这是正午的阳光,新鲜而明媚的一天,这是无数日子中的一天,却是娘的最后一天。他想了想,还是冷静地到街上打回来一扎新鲜的扎啤,也放在娘的床头,让酒香和水果香弥漫起来,他才去找来纸和笔,还找来娘喜欢的檀香点上,给她换上墨绿的袍子,整个过程,他干得利索,没有大呼小叫。
现在,他还欠娘这一幅画。从此之后,他将重新成为无父无母的孤儿,而娘已是彼岸世界的住客,此生再无牵连。内心早已泪水滂沱,脸上却维持淡淡的笑意。他要把手里的活干得漂亮,为了给娘留下最后的形象,也为了这最后的告别。
他没有想到这一天的来临会如此迅疾,又如此庄严。他以为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没什么能让他感到惊奇。可当他收好画笔,打电话通知亲友告知娘的死讯时,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他一边哭,一边与一个耳背的远房亲戚在电话里描述了娘平静而离奇的离去。挂了电话,他搬了一条板凳,坐在娘身边,等他们来。暮色降临,房间里越来越冷,而亲戚们还在来的路上,远没有抵达。恐惧像夜雾一样包围了他。随后,他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黑暗的房间里嚎啕大哭起来。
载于《芝罘文艺》年第1期
芝罘赞赏